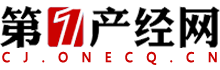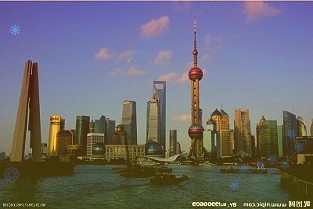那时,我还小。生活在乡村,不过,我那个乡村是一个公社所在地,要比一般的乡村热闹。少时,全村人和同公社其他村的农民一起热闹,人人都是诗人,个个会编顺口溜。贫下中农管理学校,老师没有更多的学问可以传授,就画漫画;农民很欢快,公社大礼堂上,堂兄扎着长棉布腰带,上去唱“三句半”。我知道,乡党很少过国庆节,更多的是“吃国库粮”的过国庆节。公社大门上张灯结彩,有红对联贴出来,公社前面的公路上有乡亲们晒的瓜干和花生。正是收获的日子,这时会有电影放。我那时不过六岁,一大早会在电影场上“护地方”,放《英雄儿女》,还有新闻加影片。有一次放成昆铁路的新闻,有人说隧道里的那个吹哨子的是我父亲。父亲有一次回家,我向父亲求证。父亲说,那不是他。他在成昆铁路线上是盖房子的。

父亲一年回不了一次家,有一次,我拿着錾子要打父亲,父亲不相信我会打他。我就狠狠地把錾子打向了父亲的头。在铁器面前,肉是扛不住铁的。一家人架着父亲走向医院,我躲在麦垛里不敢出来。多年以后,我看着父亲头顶的伤疤,心里还会隐隐作疼。父亲没有打我一巴掌,他修铁路,一两年才能看一次孩子。等我到铁路工程队工作,有一年国庆节,父亲坐货车到徐州看我,我竟然没有管父亲的事。我不知道父子之间的情谊,该是一种怎样的感情?只知道,收获的季节会有一个国庆节。在乡下,中秋吃过了月饼,月亮亮过了,柿子就红了,地瓜就该收了,这时父亲就会从铁路工程队赶回家了。
我终于接了父亲的班,去铁路做了一名建设者。由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,离不开大地,也离不开庄稼。此后,每年的国庆节,我都会到工地附近的庄稼地里走一走。国庆节前,工程队会插几杆红旗,红旗随风飘扬。工地旁边的田野里会刮来新翻土地的味道。有花生和红薯,也有梨和苹果,当然也有金黄的南瓜,工程队门前的葫芦也会悬挂在那里。工程人四处行走,线路在延伸,我那时最喜欢去铁路慢车上接一份报纸。国庆节我会在工地上过,有一年,单位三产做的月饼卖不出去,发到工程队。老鼠们在这边吃,我在旁边和它们比赛,看谁吃得快。
我赶上了铁路大提速,也坐上了高铁。而父亲在提速之前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年国庆节过后一个多月,我在工地上莫名其妙地泪如雨下。很快收到家里的电报,父亲去世了。看着父亲头上的伤疤萎缩成黄色,我哭得死去活来。别人问起伤疤的来历,父亲从来微笑不语。父亲永远不能再这样微笑了。
乡亲们和我一起送父亲到戴家林,父亲的坟,依山傍水。他干了一辈子铁路工作,提速列车没坐过,高铁更没有坐过。京沪高铁开通时,我怀揣父亲的照片,让父亲与我一起感受高铁。
中秋节,是中国人必过的节日,过完了中秋才会过国庆节。今年,家乡那幢破败的老屋被妹妹盖起了楼。公社改乡后并入了另一个镇,再也看不到大路上的电影场了。邻居的哈巴狗,也学会了拨弄手机屏幕。
又一个收获的季节来临,我看着蓝蓝的天,品尝着又香又甜的边疆大柚子。秋天爽朗的气息,此刻正洋溢在京城的每个角落。又一个国庆节快来临了。